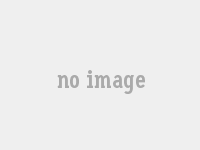有一位著名文学评论家,曾经教诲公安作家们:要努力创作史诗型的作品,要为中国公安写史。他的话语恳切、郑重,闻者无不为之心潮澎湃、跃跃欲试,同时也深感力有不逮,深知责任的沉重。
巴尔扎克有句名言: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在他看来,文学作品的史诗性,是创作的必然。当代中国评论家谢有顺先生有类似的观点,他说,小说是活着的历史。小说的存在其实是为了保存历史中最生动的、最有血肉的那一段生活,以及生活中的细节。其实,两位的说法应该并不仅仅局限于小说,古今中外的史诗,有许多是以诗歌,甚至是以口头吟诵的形式留存至今的。如《荷马史诗》《罗摩衍那》等,都是著名的史诗,是世界文学史上的瑰宝。创作具有史诗特质的伟大文学作品,是每一位作家的梦想。
史诗为什么是史诗?大概大家所能公认的,应该是以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恢宏漫长的发展史为背景,铺陈开来的一段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的故事。在近现代文学史上,哥伦比亚的《百年孤独》,美国的《飘》,苏联的《静静的顿河》,应该都可称之为史诗型的鸿篇巨制。我们更熟悉的《白鹿原》,以陕西黄土高原上自封建社会向民主社会推进的历史进程为背景,以白、鹿两大家族的恩怨情仇为故事主线,突出的是中国农民继承千年的传统与新时代带来的觉醒之间的碰撞与厮杀。有人评论说,《白鹿原》是中国农民的史诗。我深以为然。
然而史诗仅有宏大的背景和吸引人的故事是不够的。史诗之所以是史诗,还在于它应成功地塑造出丰满、生动,与故事所处时代紧密相连的人物形象。如果没有斯佳丽的坚忍不拔,《飘》对南北战争的描述也许就会流于轻薄;如果没有葛利高里的万种风情,《静静的顿河》上的风景也就少了许多生动。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与记录者,人物更是文学的灵魂。我常常读到一些作品,感觉作者是在向史诗方向努力,但人物的苍白和重复,以及人物和历史有意无意的割裂,往往使他们的努力功亏一篑。文学是要面对读者的审视的,任何遗憾都无法弥补。
之前在中国上映的美国影片《敦刻尔克》,就是这样一部略显苍白的遗憾之作。作为二战期间的重大事件,敦刻尔克大撤退完全可以拍成一部震撼人心的史诗之作。但导演诺兰尽管有《盗梦空间》《星际穿越》等名作在前,在这样的历史题材面前仍然表现得捉襟见肘。特别是在人物的塑造上,鲜有鲜明的人物特征和性格表现,十几个主要人物在近两小时的时间里很难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应该说,那位老船长道森,在当海军征用他的游艇时,拒绝水兵上船,而单独驾船赶往敦刻尔克的细节,是这部电影中最能表现人物性格的一幕。只可惜这样的细节寥寥无几,更多的是人物跑来跑去,让观众分不清面目。40万盟军在敦刻尔克的悲壮大撤退,在银幕上留下的只是商业化的浮光掠影。
那位有远见的评论家,应该说在中国公安作家们的心中植下了一个梦。中国公安事业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确实是一部壮烈而雄伟的史书。为中国公安写史,应该是我们的梦想,更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是我们几代公安文化人的责任。从历史长河中撷取丰富的营养,塑造出鲜明的中国公安英雄形象,书写中国公安的史诗,目标在前,职责在肩。
巴尔扎克有句名言: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在他看来,文学作品的史诗性,是创作的必然。当代中国评论家谢有顺先生有类似的观点,他说,小说是活着的历史。小说的存在其实是为了保存历史中最生动的、最有血肉的那一段生活,以及生活中的细节。其实,两位的说法应该并不仅仅局限于小说,古今中外的史诗,有许多是以诗歌,甚至是以口头吟诵的形式留存至今的。如《荷马史诗》《罗摩衍那》等,都是著名的史诗,是世界文学史上的瑰宝。创作具有史诗特质的伟大文学作品,是每一位作家的梦想。
史诗为什么是史诗?大概大家所能公认的,应该是以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恢宏漫长的发展史为背景,铺陈开来的一段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的故事。在近现代文学史上,哥伦比亚的《百年孤独》,美国的《飘》,苏联的《静静的顿河》,应该都可称之为史诗型的鸿篇巨制。我们更熟悉的《白鹿原》,以陕西黄土高原上自封建社会向民主社会推进的历史进程为背景,以白、鹿两大家族的恩怨情仇为故事主线,突出的是中国农民继承千年的传统与新时代带来的觉醒之间的碰撞与厮杀。有人评论说,《白鹿原》是中国农民的史诗。我深以为然。
然而史诗仅有宏大的背景和吸引人的故事是不够的。史诗之所以是史诗,还在于它应成功地塑造出丰满、生动,与故事所处时代紧密相连的人物形象。如果没有斯佳丽的坚忍不拔,《飘》对南北战争的描述也许就会流于轻薄;如果没有葛利高里的万种风情,《静静的顿河》上的风景也就少了许多生动。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与记录者,人物更是文学的灵魂。我常常读到一些作品,感觉作者是在向史诗方向努力,但人物的苍白和重复,以及人物和历史有意无意的割裂,往往使他们的努力功亏一篑。文学是要面对读者的审视的,任何遗憾都无法弥补。
之前在中国上映的美国影片《敦刻尔克》,就是这样一部略显苍白的遗憾之作。作为二战期间的重大事件,敦刻尔克大撤退完全可以拍成一部震撼人心的史诗之作。但导演诺兰尽管有《盗梦空间》《星际穿越》等名作在前,在这样的历史题材面前仍然表现得捉襟见肘。特别是在人物的塑造上,鲜有鲜明的人物特征和性格表现,十几个主要人物在近两小时的时间里很难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应该说,那位老船长道森,在当海军征用他的游艇时,拒绝水兵上船,而单独驾船赶往敦刻尔克的细节,是这部电影中最能表现人物性格的一幕。只可惜这样的细节寥寥无几,更多的是人物跑来跑去,让观众分不清面目。40万盟军在敦刻尔克的悲壮大撤退,在银幕上留下的只是商业化的浮光掠影。
那位有远见的评论家,应该说在中国公安作家们的心中植下了一个梦。中国公安事业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确实是一部壮烈而雄伟的史书。为中国公安写史,应该是我们的梦想,更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是我们几代公安文化人的责任。从历史长河中撷取丰富的营养,塑造出鲜明的中国公安英雄形象,书写中国公安的史诗,目标在前,职责在肩。